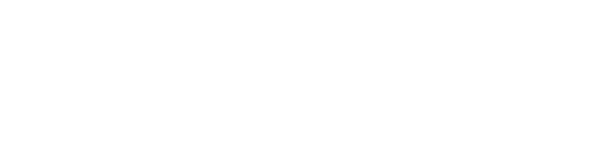我的1978年高考
![]() 学习报联商,改变自己的职场环境 40-46# 2019.05.13-31连载发表于报联商读者群
学习报联商,改变自己的职场环境 40-46# 2019.05.13-31连载发表于报联商读者群
群主按:
即将到来的6月初,全国又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,看着那些紧张备考的孜孜学子们,不禁想起41年前我自己的高考。
早年曾写下过一篇回忆录。去年春季,在我参加高考40周年时,也曾向出版界的朋友询问过:能不能找到哪个媒体发表一下?人家答曰:如今都是自媒体时代了,要发表就自己发表吧。
一晃又是一年。现在,又到了高考季,也许是年龄大了?还是忍不住要发表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当年。那,就在自己的群里发表,和大家分享吧。
希望朋友们不要嫌弃,如果觉得“老生常谈”,不看就是了。
我觉得这也是在普及介绍“报联商”---- 通过此文,让群友/读者们了解作者走过的人生之路,负笈东渡的求学之路是如何起始,远渡东洋取回“报联商”真经 也是多么的不易。
本文拟分七小节,自5月13日开始,分七次连载到6月初高考前夕结束。
古贺 传浔
书山有径勤为路,学海无涯苦作舟
—— 我的1978年高考
大家都知道我这一辈子是吃日语饭的,可是我又是怎么和日语结缘的呢?说来竟然好笑。我是在文革之中,知识无用论横行的年代开始跟着收音机学习日语的。谁知道,这一学,就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。
1. 与日语结缘
那是1976年5月。我当时已经25岁了。
刚刚过去的4月,发生了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天安门事件,邓小平再次被公开打倒,全国一片批邓 / 声讨邓小平复辟的浪潮。那时人们看不到国家的前景,更无权安排自己的命运,一切都只能听从党的安排。
业余时间里,人们只好用打扑克,拱猪(现在的斗地主)来消磨时光。我也曾经是彻夜扑克族,打得很上瘾。但是,打了一阵之后,觉得很无聊,心里空落落的,总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。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,内心很迷茫。也找不到个什么人可以商量前途,所以很苦恼。
当时我在一个汽车队做修理工,每天干修理汽车的活儿,钻汽车底,抬发动机,卸轮胎,调刹车,车钳铣刨泥瓦木,板金水管电/气焊,什么都干……,一身油包的工作服。
有一个周六,下班时,单位管人事的大姐犯了头疼病,我们几个单身汉大小伙子,把她抬上单位的一辆汽车给送回家去。到了她家安顿下来,却听见放在床上的半导体里正在播放「あ,い,う,え,お」的发音。我问,这是什么?回答说是她念初中的女儿在跟着收音机学习日语,这个星期刚刚开始。
原来,中日自1971年10月建交以来4年多了,和日本的交往日益增多,老一辈会日语的人已经陆续老去,国家急需新的日语人才。当时的大学虽然已经部分恢复,但招上来的“工农兵学员”在校学习的大多是政治。而且很多教授讲师都还在“牛棚”里接受“改造”,没被解放,学校的师资队伍人才奇缺,在校生的专业课程水平因此受限。所以,收音机才开设了广播函授的日语课程,面向广大听众授课。
也许因为我的父亲是教师,从小就受到“唯有读书高”,“艺多不压身”思想的影响吧,在闲极无聊之中,碰上这种广播函授课程刚刚开班,管它学的是什么呢,心想:学点什么,总比闲呆着混日子强吧。抱着这一想法,我就打算开始跟着学。
一问人家,说已经开班一个星期了。于是,转天的周日上午,就跑到市里的外文书店去买课本。哪里还有?早卖光了。硬是跟柜台的售货员说好话,人家只好把书架留样的独本样本借给了我。当场趴在柜台上,把课本上的第一课给抄了下来。那时根本不懂日语,完全是照葫芦画瓢的描(说“画”也许更贴切些)那些弯弯曲曲的日语假名。
好在是每周一,三,五讲一节新课,二,四,六则重播前一天讲的内容,周日再全面重播这一周的三节课。平日中午12:30到13:00播第一次,晚上19:00到19:30重播一次。第二天完全重播前一天的同样内容 ------ 这是照顾函授学员的特点,进度很慢。
那个周日的上午,在书店抄了书,赶回家中补听中午的一周重播,晚上再听一次重播,第一周讲的内容就这样看着抄来的课本给补上了,可以说是咿呀学语。
第二周继续讲第一课(函授课都是好几周才讲完一课的)。几周过去,第一课讲完了,去书店看,还是没有课本,就又在那儿把第二课的内容给抄(描画)了回来,又能凑合几个星期。
2. 闷头苦学
在车队上班,中午休息只有一个小时。每天12:00下班的铃声一响,我连工作服都不换,就这么一身油包的,骑自行车用9分钟飞驰回家。那时家里就妈妈和我这个老儿子娘儿俩过日子。我做饭手底下非常麻利就是在那个时期练出来的(妈妈有高血压的病,做不了饭)。回家脱掉外衣就动手做我和妈妈的中饭。两人的一饭两菜一汤到12:30左右,基本上可以端上饭桌,马上打开收音机,边吃中饭边认真地听12:30到13:00的第一讲。到了12:50分时,把妈妈扶持上床睡下后,连碗都堆在桌子上来不及洗,就又得骑车飞奔回去上班。
晚上17:00下班。那时还有“天天读”一个小时(政治学习:读毛主席的红宝书,读报,紧跟形势批判邓小平……),还几乎天天晚上停电。回到家是18:15了,这才比较从容地洗中午的碗,作晚上吃的饭。1976年时还没有煤气,家家都是点煤球炉子,要是中午走时没封好火,炉子灭了的话,还要重新生火点炉子!19:00到19:30分当天的日语讲座重播,是我这一天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听全了的一讲。晚上收拾完家务活之后,就自己自习日语。
那时周围也没个老师,更没有个同学。我自学日语在单位里也不敢声张,不能让领导和工友们知道,否则会批判我不务正业!我当时又是单位里共青团的委员,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怎能不“突出政治”,而去学洋文?
学习呢,也没有个方法,就是听课,一遍一遍地抄写单词,默写单词,抄写课文,默写课文,然后背课文。也不知自己的发音对不对,也没个同学给纠正。自己做课后的作业,对照正确答案时发现做错了,也不知道错在哪儿。
就这么地凑合学下去吧,谁知,刚讲到第五课(也就是日语的各种发音刚刚讲完的时候),1976年7月28日,发生了唐山大地震!中央广播电台的这套讲座播不下去了。接着9月9日,毛泽东主席逝世!这一停课,就是两个多月。
这段时间,我干脆跑到外文书店去,趴在柜台上抄人家那册样本。这回有时间了,干脆一模一样地抄(描画),连每一页的版面都抄成一样 ----- 书上的这一行/这一页到哪个字结束,我也就抄到哪个字。好在两个多月的学习,写单词,抄课文,已经把日语的假名和字母们写得有点模样了。
结果到10月份(时逢四人帮被抓捕后)再恢复播讲时,我硬是照葫芦画瓢地把第一册的课本生生地手抄了一册下来,连封皮都照猫画虎地画了一张,规规矩矩地加上封面,制本装订成册地自制了一册课本!(后来前院王老师说她的孩子要学习日语,找我借去了这册手抄本,没再还回来,每当想起一直是很惋惜的。)
1976年10月恢复播讲时,为照顾全国听众,又重新从头来过,再教一次A, I, U, E, O 的发音。这,对于我这种大龄学外语的人来讲,太好不过了!这回更加认真地听讲,巩固了发音基础。
那后来就接着学下去了,从第二册的课本开始,就自己提前去书店买到手了。其实广播函授学习的规律都是开班第一册时人们一哄而上,越到后面能继续跟进的人越少。
学习一直都是自己学,既没有同学讨论,也找不到老师当面给指点,真是不知道自己学得怎么样,连读课文的发音对不对自己都不知道。
学到语法阶段,难度逐渐加大。函授讲座的进度每天虽然很慢,只讲一个句型,或一个惯用型,一个词尾变化等,但往往是这节课的内容还没来得及消化,下节课又接踵而来!(没有同学,没有老师,只是自己听声音学习,仅业余那点时间,年龄又大了……),日复一日地,慢慢出现了耳朵虽在听课,脑子却跟不上转的现象,感觉到学习如“负重登山”。
无奈,晚上自己自习时便想了一些学习方法:把助词的用法呀,动词的变化呀,形容词的词尾变化呀,惯用型句式呀,反正课文里讲过的重要语法现象都做成自己看的懂的大表格,用粗粗的黑笔写在挂历纸的背面(那年代百姓能找到的大型纸张也就这个了),用扣钉钉在墙上,吃饭时耳朵听收音机里讲语法时,眼睛就盯着那些表格,寻找相应的语法现象看着,来辅助听课 ----- 要不然脑子就跟不上转!
于是家里墙上贴了很多这种大表格,像大字报(这些东西现在还珍贵地保留着)。那时妈妈还能说话,“日本语”三个字的发音是“尼虹窝”,吃饭时指着墙上的那些表格问她那是什么,她说是:“你哄我”。
这样艰苦地学习了一年后,1977年7月,妈妈高血压的脑溢血再一次复发,又住院了。陪伴妈妈住院的那40多天,晚上下班后就去医院的病房(地震后在医院的院子里搭的大帐篷病室,几十张病床)。到上课的时间了就插上耳机听课。晚上在院子里的路灯下自习后,就那么和衣斜歪在妈妈的病床脚上,打通腿睡去,反正20来岁的单身小伙子,没那多讲究。
这次妈妈没能像以往多次住院那样,经治疗之后再站起来,终于彻底地瘫在了床上。妈妈出院回家后,我的生活担子更重了 ----- 每天妈妈的吃,喝,拉,撒,屎,尿,洗,涮都要由我来照顾。晚饭后为了能尽量设法恢复她双脚的走路功能,我总要熊抱着妈妈在屋里走一阵路。
伺候妈妈洗脸,擦身(卧床不起,却一点褥疮都没有!)睡下后,我还要到院子外面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,用水桶提水回来灌满家里的水缸。当过兵的我喜欢干净整洁,每天都要把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了,再用拖把把地拖一遍,心里才静得下来,才能有心思进入我的学习。
做完这一切得21:00点了。那个年代全国也都还没有电视可看,停电几乎是每天的功课。夜晚为了省灯油邻居们睡得都早,平房的大院子里,各家各户的窗户黑黑的,只有我的窗户亮着小小的油灯,我开始复习白天跟着收音机听的那点儿内容,进入日语的世界,沉浸在语法,变化,句型…….的海洋里,直到夜深。
从我25到27岁(1976-1978)两年多的青春时光,我就是这样 ----- 不搞对象,没有娱乐(那年头若不打牌,也真的没什么娱乐),白天上班修理汽车,下班回家照顾半身不遂的妈妈,晚上坚持着业余时间自学日语,就是这样度过的。学习日语占去了我几乎所有的夜晚业余时间,再也没打过扑克了(围棋偶尔还是要下的)。
现在回想起来,说是热爱日语吗?也谈不上。只不过是在打发青春过剩的精力,消磨多余的时间罢了,也没有什么坚强的意念,更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,就是靠一股子“得学点儿什么,不学不行”的极朴素的想法支撑着自己,真的没有什么目的,真的。
3. 报考,备考
这期间,国家粉碎了四人帮,结束了文革,万事开始拨乱反正,意识形态里开始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,经济建设开始了农村的承包到户,国家开始从文革的浩劫中全面复苏。
文化方面也从极左的禁锢中苏醒回来,于1977年恢复了高考。上大学不再靠工农兵推荐,而是可以凭个人的能力考试啦! 也许是因为在基层车队的原因,当1978年初夏我得到这个消息时,第一次(77届)的招生和考试已经结束了!而我从1976年5月到1978年的5月,跟着收音机也已经自学了2年的日语,课本也学到了第四册快完的时候(全套共6册)。
其实在1975年夏季,我倒也曾参加过一次工农兵学员的考试。记得那次只考一道政治题:“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,讲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促进生产的最大动力”。8开纸的卷子,我是正反两面洋洋洒洒地给它写了个满满当当,大讲修理汽车时的活思想,后来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,克服了困难,云云…….)。但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,加上当时上边的计划是在我们公司招一名会计,而我报的是天津大学内燃机系,从而我没有被录取。略表过不提。
1978年春季,我得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后,立即决定报考7月份的全国统考。
当时我在车队正好在学习驾驶(脱产两年)。一天跟师傅上路,练开车。一天在车队,带领6名工友学修理汽车(那时的驾照是需要会修车的,要考试的),执照就快要拿到手了。复员军人嘛,单位的骨干力量,所以我即是基干民兵,又是团干部。以这种身份,正面去跟单位要求报考大学的话,单位是不会给我开介绍信的(那年头,没有组织盖上大红章的介绍信是寸步难行,什么事也办不成的)。
这一回,又是最初的那个人事大姐起了作用 ----- 我暗地里在偷偷自学日语,单位里没有别人知道。有一次冬天,轮到我们这组学员上路练驾驶,路过我家时,教练师傅和工友们进我家去灌点开水。师傅和工友们进屋看见我家里墙上贴的那些外文表格,问我:这是什么呀?我说是哥哥在学外语,给敷衍过去了。
可是,那个人事干部大姐因为她的女儿也在学,是知道我一直在学习日语,并没有中断的。于是,我就跑去私下里跟她说:我不过是想借这个机会,通过考试让老师给打打分:看一看自己这两年到底学到了个什么水平。得个高分呢,就会有点成就感,如果不及格呢,就再努力。而且保证:我只是到了第三天下午才请假,只去考个日语单科就罢。这么一说,她就给我开了介绍信。我是这样才得以报上名,也算是走了个后门吧。
最初的想法太简单不过了:真的是想只考外语这一门,只去一个下午就行了!我内心仅仅是想借这个机会,通过考试让老师给我的自学成绩打打分,想看看自己这两年的自学到底学到了个什么水平。自学两年来,总算第一次找到个机会,能利用参加考试的方式,跟某位懂日语的人交流一下了(真的很渴望找到知音)。当时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,也没有人能给我指出这将是一件影响我人生的特大事件。
报上名以后把这事跟我的三姐讲了。三姐是师范毕业,在中学当物理老师。她就劝我:反正两块钱也花了,不如六门都去考考看。能歇三天公假,在家呆着也是呆着。我想想倒也是这个理,于是这才想全面地去考一考。
另外,我也还有点私心:说实在的是心疼那两块钱的报考费。尽管我当时一个心气地只想去考外语这一科,但是人家一报考就得交2元钱的报考费。这对于一个月工资36元的人来讲,一次性花掉月工资近6%,可算是份大花销了(那年头看场电影5分钱)。花这么多钱却只考一门,岂不是亏啦?考试要考六门功课(语文,政治,数学,历史,地理,外语),哪怕是只参加第三天下午的外语考试,我也可以借此歇三天公假不必上班。如果我六门全去考的话,单位也不能不准我的假,这好歹也对得起那2元钱的报考费呀。真的,现在听起来这种想法好可笑,难逃占公家便宜的嫌疑,可我当年就是这么想的(思想水平真低)。
再说,我当时在单位里修汽车已经5年,算得上一把好手了,该会的技术都会了,从心里不愿意再去重复干那每天都一样的活儿,正在自己闷头进行修车工具的技术革新 ------ 反正就是有点不愿周而复始地重复每天过同样的日子,想换个活法了。
定在7月初的考试,这时已进入6月,没多少时间了。既然去考就得复习呀,可哪还来得及?白天要上班,晚上伺候妈妈睡下后跑到三姐学校去,那时她们几家没房户的老师,1976年8月唐山地震后到了1978年的夏天,都两年了,还住在学校在操场后面给搭的临建房子里。隔壁就是数学老师,语文老师的,方便倒是蛮方便的。
夏天嘛,吃过了饭,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,受到拜托的老师开始先给我摸底,准备好对症下药地进行补习。可是我文革前只上到了初中二年级,三角,几何根本就还没有学到,经过十年的文革,连怎么解一元二次方程式都忘得干干净净!老师看了看我的底子直摇头 ----- 这课是真不知从何补起。姐姐,老师和我,大家都哭笑不得。
结果,这仅有的一个月备考时间,一天班也没歇,不敢请事假备考呀,怕漏了馅被同事们知道了嘲笑。
好歹到了考试的日子,事前政府有文件发下来,各单位不得阻挠考生应试,所以我得以顺利地三天都能有公假去考场。可是这一来,同车学驾驶的工友们也就都知道了。我只好又以看看自己水平为借口敷衍一气。毕竟那时候《知识越多越反动论》,《知识无用论》还没来得及被拨乱反正过来,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。
同时,也没觉得自己能考得上。至于考上了去还是不去(妈妈瘫痪在床),更是根本都没认真想过。所以,还是先留好后路再说。
4. 考场窘迫
7月7日上午,第一场考政治。我那时哪懂马哲呀?早上4点起床,楞背了一通书就去了。进了考场发下的卷子一看是16开纸(相当于现在的B5尺寸)连在一起的四张,其中一张上印得有考题。题目忘了。我的答卷可是洋洋洒洒,写满了正面3页还言犹未尽呐,又翻过来把背面4页也写满!正反两面写满了7页纸,最后一个交的卷子。
可是后来发榜才知道,如此努力,还是没及格:仅得了59分!也许是判卷子的考官看到这名考生笔走龙蛇,虽然是洋洋千言,可却离题万里,实在是没法子给及格。可是在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里居然能写出这么多的文字来,而且语言通顺,可见此人起码是思路敏捷,手没停笔,就这份辛苦也不好不给点分吧,可又不能违反纪律给及格呀,所以才给的59分吧?(这仅是我的瞎猜)。
上午考完出得考场是11点,骑车赶回家去给妈妈做中饭。从考场的学校骑自行车到家是11:20,照常做饭,扶持妈妈吃饭。吃了饭,下午是14:00考数学,觉得比平常12:09分到家,13点要赶到单位去上班从容多了,可以睡个午觉再去!
中饭时外面下起了雷震雨,早上起得太早了,好困!哗哗的雨声中,立即沉沉睡去,这一觉可睡过了头!跳起来赶紧骑上自行车往考场赶。雷阵雨虽然停了,但马路上积了水,立交桥地道里的积水更是没膝。不管它,猛蹬几下冲将过去!
好不容易自行车趟着积水赶到了考场,还是晚了,卷子都发下去了。指着绾到膝盖以上的裤腿和一身的泥水,在门口指着那张位子上空空的桌子右角贴着的考生号,拿出我的准考证和监考的老师说,我就是这个座位的考生……。好说歹说地对付了半天,人家才让进了考场入坐。
喘息未定,眼看考卷,浑身上下摸个遍,才发现竟然一支笔也没带!于是举手:“老师借您的笔用一下行吗?”
尽管我是竭尽全力地,非常认真地对待了这张数学考卷,而且也是努力到了最后,又是坚持到最后一个交卷。但发榜时才知道我这一场忙活,只得了区区8分!—— 连圆锥体的体积都不会算了!
好在后几门是我的强项,什么语文呀,历史呀,地理呀的,出了考场还有点自信,可是最后那一场关键的外语可要了命了。那题目现在看来很简单,可当时就是不懂呀。记得有道题是个俗语翻译:“手を焼く”。其实意思就是不好办,只要答“棘手”两个字就是满分。我看不懂呀,于是就写:“手”是名词;“を”是助词,而且是宾语助词;“焼く”呢,是个五段自动词,它的词尾应该如何如何变化…..,等等,整个一个给人家讲起语法来了,倒是扬长避短了。
当时在考场上心想,费尽巴力地跑到这儿来,总不能交白卷吧。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吧,管它的呢!于是,吭哧吭哧地写了两个钟头,又是最后一个交的卷子,把自己知道的那点日语知识都写上去了,真是货真价实地“使尽了浑身解数”。
结果,外语这门主科考了多少分呢? 47分!
就这,还考进了大学,而且还是以“优异”的成绩“超破格录取”呢!
不信?听我慢慢道来。
5. 居然考上了!
进了大学后,一年级下学期时,有一次我们的老师(工农兵学员留校,只担任低学年教学)和我们谈起了当时他们被派去判卷子时的难处:1978年初招生的77届已经把当年外语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几乎都给收进来了。政府要求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得招生两届(年初1月份招的算是1977届,7月份考的这批算1978届),而当时学校里的高中生们,刚从学习毛主席语录转向学习文化,还没什么实力可以竞争,于是夏季招生的这批78届,只能是以面向社会人员为主要招生对象。
可是十年文革中《知识反动论》横行,和日本建交刚刚6年多,广播函授也才试播了两年,如果不是家庭有日语背景的话,普通的社会人哪有几个人能懂多少日语呀?全国统考的卷子倒是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的,但如果真的按标准答案来判卷子的话,那可就没有人能考及格,连一个学生也招不进来了,今年上级下达给外语学院48个名额的招生任务可怎么完成呀?于是判卷老师们就此情况请示了市高教委。答复是:为了完成招生任务,只好是“沾边就给点分吧”。我们这一届学生就是这样被“优待”进大学的。
后来得知:当年全天津市报考日语专业的考生据说共有6百多人(我估计除了某学校里开了日语课程的高中班以外,就是两年前和我一起学习这轮广播函授课程的那些人)。但1978年夏季的统考,全市日语单科成绩过了60分及格线的考生只有8名!这8名考生,全被重点大学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收走了。我们被招进外语学院日语系的48人(实际报到45人)中,有13名50- 59分的人被分为第一班,我们40- 49分的16人(我成绩47分)被编成了第二班,其余39分以下的16人,统统被编为第三班。三班里外语单科最低分的人,日语只考了23分!就这,都还是“沾边就给分”才得到的成绩!------ 可见当时社会上是真的没人。
不过这种格局,仅仅维持了一年,进入二年级就打乱了重新编班。因为经过一年的学习,大家的水平基本上拉齐了。至于后来毕业时有一位进来时来被编在一班的“优等生”,竟因成绩不及格毕不了业,那是后话。
从考场上下来,我也去三姐学校和帮我补习的老师们对了对答案。其结果令我对自己的考场表现有了点自信。
填志愿更是笑话。根本不懂,随便街上买份报纸来,自己看那上面开列的学校,也不知哪个好那个坏,也没和任何人商量,就随意写了第一志愿天津外语学院日语系,第二志愿是厦门大学日语系,第三志愿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日语系。后来进了大学和老师们谈起来,才被笑话我乱点鸳鸯谱:厦门大学和北京二外都是比天津外院好得多的一流学校,哪有倒着报志愿的?
志愿也报过了,这才开始认真考虑上不上这个大学的事来。因为患病瘫在床上的妈妈还和我一起生活着,由我照顾着呢。我若上学去了,户口就要迁到学校去,妈妈的生活护理可怎么办呢?整个7月和8月我就一直在纠结此事:如果录取通知书来了,我到底是去报到?还是放弃不去?
犹豫不决,就逐个写信给哥哥姐姐们征求意见。返回来的答复都是一致的:如果考上了,就一定要去上。因为爸爸对我们7姊妹的最大愿望就是让我们都能接受大学教育。文革前,前四位哥哥姐姐都如了愿,但是一文革,我们后面这三个(一个哥哥一个姐姐,我最小)就与大学无缘了。文革期间那是没有办法,咱家出身不好,指不上人家推荐进大学,如今恢复了高考,既然能自己考上,那就一定得上,有机会一定要完成逝去的父亲的遗愿。至于妈妈的照顾,由迄今为止的大家出钱(每人每月5元)我出力的方式,改为由同在天津的二哥接手照顾,其余兄弟姐妹(包括我)出钱。为此,三姐专程召集二哥和我,转达了家族兄长们的意见,征得了二哥的同意。
事情虽然这样商定了下来,可毕竟还没有发榜,我也不知道自己考上了没有。但是第六感觉还是挺有的。7月份,将近两年的驾驶学习各科考核都通过了,我们这批同时学车的14名工友都拿到了白色实习驾照,开始各跟一辆车,上路实习驾驶3个月。既然想上大学去了,所以8-9月里实习开车的时候,不是教练车了,助手席师傅的脚底下没有了副刹车,一切情况的处理都要靠自己,于是我就特别的小心,不敢出任何事。
6. 考了第一名!
9月底,单位通知我去公司取录取通知书。也没什么特别高兴的心情,很平淡。那时并没有感觉到这一步对我的人生将是多么地重要。
拿到通知书和成绩单才知道,虽然我的外语和数学考得真不怎么样,但是其他几科很棒!历史竟然得了94分,地理得了84分,语文也得了73分。
在6科满分600分的情况下,我的总分是365分!能考出这个分数,在那一届考生里是超高分了!(相当于如今的650分吧)。
后来进了学校才知道,当年的外语类录取年龄线定在23岁以下(外语要从娃娃学起),天津外院日语系的录取分数线设在6门总分230分即可录取。特殊分数高的人可以考虑超龄录取到25岁。
我呢?是27岁录取!
如此破格录取就是靠的这365分的总分太高了的缘故。另外,第一志愿乱报的天津外院也是歪打正着了----- 档案一到天津外院,人家一看这么高分的考生(可以说是当时的状元了!)直奔自己而来,真是难得,当下就留档了。
因为那时社会上,脑袋里还能有这些知识的年轻人真是不多呢。能考出历史94分,地理84分,语文73分的人在当年几乎就是奇迹(张艺谋也是那年参加的高考。他别说考出这个成绩,根本就没及格,没被录取!后来是某领导发话才破格录取的)。开学后了解到身边的其它44名同学,尽管有的单科分数比我高,但6门的总分我的确是那一届里最高的。
别忘了10年知识无用论横行,人人都在打扑克混日子,谁读书呀?10年不读书(不过,也的确没书可读),说声考试哪能一下子就来得及把知识装进脑袋里去?那不就看这十年中平常的积累了吗。幸亏我这十年没有沉沦,没有淹没在扑克海中,平时只要有机会就找书读。四旧书都烧了/禁了,没有书读。手头仅有的一本读报手册都翻烂。毛选四卷的正文虽然只读了一遍,文后的注释却读了好几遍,那里面真的有不少知识呢。
现在回头看,当年那些考题也太一般了----- 历史,考考王莽篡位,唐太宗的姓名什么的;地理嘛,考考日地月运行关系,国际日期变更线之类的。就这,都没人答得来!那一届全国的高考录取率仅有7%!(600余人里仅选45人),能考得上的人真是凤毛麟角,被社会称为“象牙塔里的王子”啊。
9月28日拿到了通知书,9月30日驾驶执照由“白本子”(实习驾驶执照)换成了“红本子”(正式驾驶执照),也就是说我从二级汽车修理工转为二级驾驶员,工资可以从36.00元涨成39.20元了。一起学习驾驶的工友们都很高兴,那年头讲的是方向盘(汽车司机),大盖帽(警察),听诊器(医生)这三种职业最有“路子”了。因为,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这三种职业最有门路,搞得到物资(鸡蛋/肉/食油)等食品。
拿到了“方向盘”的师兄弟们哄笑我:“(天津方言)学那洋巴巴蛋干嘛?放着方向盘不用”。我也不回答,但是心里想:“燕雀岂知鸿鹄之志哉”。
就这样,过完了国庆节休假,1978年10月5日(周三)我踏进了天津外语学院的校门,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。
3年军龄加上5年工龄,已经27岁的我,以8年工龄的资格,带着每个月国家照发的39.20元的工资(叫人民助学金),读完了我的四年大学。
7. 反思,后记
Ø 现在来回想/分析一下:
l 假设再早一年,挑战(77届)呢?
肯定没戏!因为有外语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那些人压着(他们从13岁就
开始学外语啦),我们这些社会人肯定竞争不过他们。
再者,当时我的学习也还没到火候 ----- 1978年1月进考场虽然和7月进考
场只相差了6个月的时间,但是跟着收音机函授学习6个月,对我这样自学
的人来讲是多么的重要。我相信“量变到质变的飞跃”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积
累的。
l 我们这届(78届)的实况
没有比我们厉害的外语学校专科生压制我们,而当年的应届高中生们也尚未
形成竞争力 ----- 我们这一届招进来的45名学生里只有一名高中生(报到时
我27岁,他才18岁)。我的其它同学都是社会人 ----- 什么建筑工地绑钢
筋的,纺织厂的挡车工,修手表的啦,小学教师啦等等。
l 如若再晚一年(79届)呢?
也没我的份儿!那年录取的学生以外语专科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为主,普通高校
日语班的应届毕业生为辅,虽然也还有个别年轻的社会人,但那一年不论我再
考多高的分数,学校也绝不会把年龄再放宽到28岁来录取我这样的社会人了。
l 而到了1980年(80届)
那更是清一色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啦,根本就没有社会人的份儿了。
ü 如此说来,我简直就是在1978夏天,那唯一的一个适合我的窗口时间,抓住了天赐良机,几乎可以说是“钻”进了大学的—— 感谢1978年招了两届!
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我的命运吧?
现在细回想:不论是盲目地开始学习,还是匆忙报考;不论是被动复习,还是考场迟到,乱报志愿……这一沟一坎,能够坦然/ 平稳地闯过来,都是我那已于10年前去世了的知识分子父亲在指点着我,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吧?
当然,这背后也包含着我在那十年文化洪荒的环境里自强不懈地努力——偷看书,偷书看,彻夜排队去领取市图书馆的阅览证等等(均有别文另述)。否则当机会来临时,自己冲不上去,也只能是瞪眼干着急(正不知有多少同龄者顿足遗恨,望洋兴叹呢)。
回顾我的上述经历,正应了一句箴言:“机会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”。
和合(古贺 传浔)
2004年8月29日忽发写作冲动,夜深动笔,至清晨6:00一气呵成。
早就有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之愿,直至今日才得以完成,我心甚慰。
后记:
1982年从大学毕业时,正值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起步,社会上会日语的人凤毛麟角,我们这一届大学毕业生,马上被各市级政府机关抢去应急了。
后来和国际友人谈话时,时髦的说法叫为了增进中日友好才开始学习日语,其实谁又知道:至少我当时不是出于这种高尚的目的,那时开始学习日语的初衷,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已。
文革,把一切都扭曲了。想来可笑?其实可悲!
但是“天道酬勤”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这就叫做:“动锯就下沫”——努力了,必有收获;投入了,定有产出!
——路再远,只要不停地走,总能走到;事再难,只要持续去做,总能做完!
后话:
1980年代中期,我被派往日本工作,又经留学硕士之后,在日本企业就职。
世纪之交那年(2000年)我已是外企驻华首席代表兼在华子公司的总经理。
整天过的是全国满天打飞滴,入住5星级宾馆,出入乘轿车的日子。
有一次,偶遇了当年同车学驾驶的工友,得知改革大潮早已冲垮了原有的体制,我们的那个汽车队早就解散了!教练师傅才刚50岁出头就突发心梗过世了!当年同学的工友们大多转岗/下岗,有的改行,有的在开出租,有的甚至在摆地摊修理自行车!
闻听此言,脑海里瞬时闪现当年去参加高考时的景象,恰似昨日般仍历历在目。而这边厢,竟已是天上人间!
呜呼,真是恍如隔世,好一似经历了沧海桑田!
遥想当年:
如果那时没自学呢?如果没去考呢?如果真的只考了外语一门呢?如果考上了也没去报到呢?(我们那一届就有3名被录取的考生没来报到)
是命运之神眷顾了我?
还是我自己靠拼搏改变了命运?
2019年5月复核(全文完)